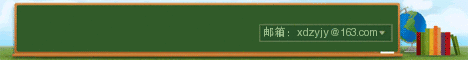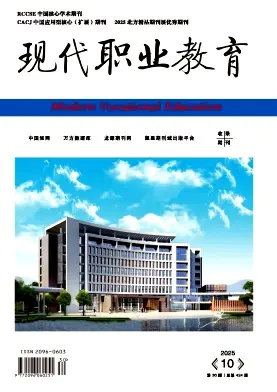【热点导读】: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发展 地下连续墙施工及渗漏水治理 土建结构工程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城市和谐治水经验启示
1日益频繁与严重的城市水患发人深省华夏自古多水旱,近年来,还呈现出极端气候增多,洪涝频繁且灾情加重的趋势。1998年6月中旬至9月上旬我国出现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长江流域及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全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550亿元[1]。2010年又出现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泥石流、山洪较往年更为严重,舟曲等地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损失巨大,至当年8月,直接经济损失已逾2000亿元。2011年入夏以来,因暴雨导致的城市“内涝”现象更是愈演愈烈,6月23日,因突降暴雨,北京多处路段不能通行,汽车被困水中,地铁告急,7月3日的强降雨使成都内涝严重,交通瘫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武汉、长沙、杭州,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在暴雨之后陷入“看海”的窘迫与无奈。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351个城市进行的城市排涝能力专项调研,2008~2010年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其中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范围甚至扩大到干旱少雨的西安、沈阳等西、北部城市;在发生过内涝的城市中,最大积水深度超过50cm的占74.6%,积水时间超过半小时的占78.9%,其中有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2]。如此普遍与严重的城市“内涝”现象引发了市民广泛的关注与质疑,耗资巨大的城市建设,为何“逢雨必涝”?如何解决?其实每个城市发生“内涝”的原因不一,或为江河水倒灌,或为暴雨时来不及排走大量积水,或为局部地区选址不当,笔者认为城市“内涝”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是靠越筑越高的堤坝、越来越粗的排水管道和马力愈强的水泵就能解决问题,它事关城市规划建设理念与管理,需要整体、系统地考虑。中国自古以来就水旱频繁,城市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治水”史,通过回溯我国数千年的治水史、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剖析那些经典案例所蕴含的哲理,应该会对当今城市建设有所启示。
2从治水历史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地理环境的形成经历了极其漫长的由海变为陆地的过程,远古时期,总体为南海北陆的格局,华南地区均为大海,大约从二亿年前三叠纪开始的“印支运动”结束了南海北陆的局面,形成基本的大陆环境,之后,“水”也是一直影响我国城市建设的重大因素。按理念与技术的差异,我国治水历程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①:完全依附自然的原始阶段;顺应和改造自然的古代阶段;试图征服自然的近现代阶段;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的当代阶段。这四个阶段实质上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由“依附—顺应—改造—征服—和谐”的变化。夏朝建立前后的一二百年间,也就是传说时代的五帝之世,是华夏洪水泛滥时期,我国古代各地广泛流传的女娲补天神话,水神崇拜、祭天求雨等反映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的依附,当时治水主要靠“堵”,收效甚微。秦汉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带来技术的进步,人类开始改造自然、控制江河,是治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其中,建于秦代的都江堰,建于宋代的以福寿沟为代表的江西赣州城市排水系统所反映的整体、系统、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尤其值得当代城市借鉴,而“水淹泗州城”的沉重教训则对我们有所警示。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引发了水利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需要也对水资源的治理与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时期人们通过水库、渠道、大型堤防等水利工程,更大程度地控制了大江大河的洪水,大面积的城市防洪排涝开始建设,但也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带来严重灾难的现象,此外城市发展过程对生态的破坏也加剧了水患。21世纪以来,人们认识到让“高山低头,江河改道”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主动协调人与水的关系,以期达到利用自然、修复自然、维护自然的目的,力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上阶段反映了我国数千年来治水理念与技术的传承、发展与转变,其中既有无数的失败与教训,又有从中总结的宝贵成功经验,以下选取几个典型案例,剖析其中蕴含的哲理,总结经验与教训,进而探讨对当前城市建设的启示。
3历史治水经验与教训剖析
3.1大禹治水:从“堵”到“疏”的历史必然《孟子?滕文公上》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时治水主要靠“堵”,收效甚微,但成功也在长期的治水失败挫折中慢慢孕育,转变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禹之时,十年九涝”(《庄子?秋水》),大禹改“堵”为“疏”,取得了成功。同时期的古蜀(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世纪)也有相似的经历,据古气象学研究,距今3000年以前,长江上游雨量充沛,年温比现在高2~3℃;成都平原在5~10月的雨量约占全年的85%~90%,洪涝之灾史不绝书。蜀王杜宇之时曾遭受“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蜀王本纪》),“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华阳国志》)。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治水实践,先民们已开始从完全依附自然向顺应自然过渡,由“堵”变“疏”的治水方法取得成功并开始传播,对后来的治水理念有着重要影响。
3.2都江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哲理都江堰的修建源于两千多年前,岷江每值春夏屡屡引发洪灾,东旱西涝,洪水退后,沙石遍野,整个成都平原均为水患困扰。秦以前的古蜀治水多为“堵”,效果甚微,公元前3世纪后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根据对地形和水情的实地勘察,吸取开明氏的治水经验,主持修建了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的都江堰[3]。该水利工程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当地地形、水势条件,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一条排洪,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实现自流灌溉,变害为利,主要通过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几大主体工程现这一目标(图1)。治水的关键环节首先要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流向东边,一方面减少西边江水流量,同时也解除东边地区的干旱,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宝瓶口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有一段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又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江心筑鱼嘴分水堤,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防止进入的水量忽大忽小、又在鱼嘴与宝瓶口之间,修建了“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经由堰顶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同时利用宝瓶口前面三道崖的弯道环流地形和水势,使洪水中夹带的大部分泥石流入外江,有效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都江堰水利工程从区域角度,充分利用了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地形、水势,因势利导,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形成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的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体系,不仅从根本上疏导了洪水,还解决了灌溉问题,特别值得现代城市借鉴。
3.3福寿沟:实用而巧妙的防洪排涝体系(图2)2010年夏季的持续暴雨使广州、南宁、南昌等诸多城市深陷“内涝”之苦,附近的赣州市部分地区降水也近百毫米,老城却安然无恙,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事实上赣州三面环水,宋朝之前,也饱受水患,今日老城不涝还得归功于北宋时刘彝主持修建的以福寿沟为主的城市防洪排涝系统,这套系统不仅实用还很巧妙,对城市“内涝”有很大启示。首先沟渠体系利用了地形,靠重力自然排水古城根据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布局福沟和寿沟(因两条线路走向形似篆体“福”“寿”二字而得名)两个排水干道系统分区排水,合理利用地形高差,雨水、污水可以自然地由城中高地排向周边的江或塘里,沟总长约12.6km,其中福沟11.6km,寿沟约1km,沟为砖拱结构,宽约0.6~1m、高约1.~2m[4],足够排水,也便于检修。其次,福寿沟和城内的几个大池塘,几十个小塘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图4)。这些池塘或为城内低洼之地,或为应防洪和军事需要,取土筑墙留下的,当城内暴雨时,可以暂时将雨水蓄积起来待江水水位降低再排走,也可留待干旱时取用,还能调节气温,美化环境[5]。位于城墙处的“水窗”设计原理简单但却十分巧妙,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即借下水道水力将水窗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力将水窗自外紧闭,以防倒灌。为保证水窗内沟道畅通和具备足够的冲力,采取了改变断面加大坡度等方法,确保水窗内能形成强大的水流足以带走泥沙,排入江中。即使在江面涨水,水位高于水窗,而城内又暴雨的极端情况下,只要福寿通过福寿沟排向江里,水塘也可积蓄一部分洪水,最大限度地保证城内不涝。
3.4“水淹泗州城”:漠视规律,顾此失彼的沉重教训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乏漠视自然规律,只顾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的历史教训,甚至有的水利工程带来或加剧了一些区域的水患,带来深重的灾难。“水淹泗州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12世纪以前的淮河是一条河槽深广、畅流入海的清水河流,具有足够的排泄能力将其流域洪水排泄入海,但元、明两代,由于建都北京,为了维护大运河南粮北运的任务(即漕运),对黄河采取遏制北流、分流入淮的策略,淮河水系因此受到扰乱,黄河泥沙的淤积使洪泽湖底和淮河河床越来越高。明万历6年(1578)推行“筑堤障河,束水归槽;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的策略,在泗州淮口下游筑高家捻,人为蓄高了淮水,泗州城长期处于洪泽湖正常水位之下一,年有十多次“水漫泗州”的大水,康熙十九年(1680)彻底被水淹没,沉入了洪泽湖[6]。正是明清两代推行的“蓄清刷黄”、“济运保漕”政策,造成黄河夺淮后的深重水灾,进而造成本就地势低洼的泗州城的沉没。被水淹没的泗州城时刻警醒我们,“治水”是一个关乎“天”、“地”、“人”的复杂系统,违背自然规律,孤立看待问题,缺乏全局观与系统观,难免顾此失彼,保了一方,危及四方。
4历史治水经验对城市“内涝”的启示
4.1统筹兼顾,增蓄减排城市“内涝”的主要原因是强降水或连续降水的量超过了城市的排水能力,造成的积水现象,有时江河水倒灌也会引起城市“内涝”。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尚为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洪涝灾害并不代表整体的水资源过剩,而是短时、局部的水过剩,并且往往是这边洪涝那边干旱,这时水灾那时旱灾,调蓄得法则水旱从人,都江堰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把多余的水排入外江流走,需要的水则引入内江作灌溉之用,变害为利。因此,借鉴成功的历史经验,着眼全局,系统地考虑“蓄”与“排”的关系,因势利导,灵活运用“堵”与“疏”等方法,是当前根治城市“内涝”的关键,首先,“蓄”住的水多了,要“排”走的水自然就减少了。我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十几次“百年一遇”的洪水,根源不仅在城市本身,在于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环境过度索取造成的生态破坏。砍伐森林破坏了水源的涵养;围湖造田蚕食了大面积湿地,降低了蓄洪能力,“蓄”的量少了,“排”的压力自然就增大了。因此,要加强流域范围植被的保护与培育,从源头上“蓄”住水;保护或恢复一些大型湖泊,统筹布局与管理水库,避免顾此失彼,充分发挥它们在中间阶段调蓄洪水的功能,防洪同时抗旱。在城市内部也是如此,不仅要排水,也要“蓄”住水,缓解缺水的问题。根据地形在低洼之地结合城市绿地规划水塘,提高城市蓄洪的能力,平时还能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