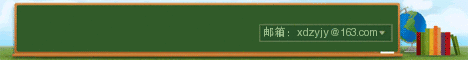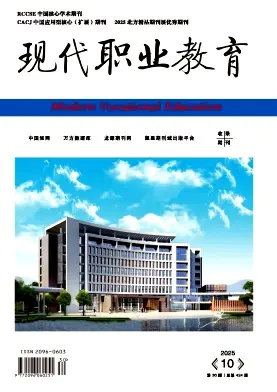中国教育改良和成长中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教育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配合存眷,被作为人类迎接21世纪挑战的首要的要害性因素,国际组织和各国当局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各类战略对策和国度决策。这种动向反应了未来社会和未来教育将会经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在未来经济社会成长中的职位和感化将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从社会的边沿进入社会的中心职位;另一方面,教育自身也将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厘革和创新,正如《世界高档教育宣言》指出的:教育将要“进行历史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厘革和革新”。因此,如何推进教育的改良和成长,为迎接21世纪做好筹备,已经成为干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正是在这种配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而且坚定不移地组织实施,相继宣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动作打算》(以下简称(动作打算》)和《关于深化教育改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召开改良开放以来第三次全教会,全面陈设跨世纪教育改良和成长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是我国迎接21世纪的教育大纲和施工蓝图,包括着重要的战略选择和理论与政策上的重大打破,是我们学习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兵器和动作指南。
一、教育在国度和社会成长中的根本性职位
教育在经济社会成长中的职位,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问题。党中央作出的科教兴国的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担任和成长,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选择。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央全面阐明国际海内成长的态势,认为必需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大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常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法和经济体制的底子转变。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一定选择,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子担保。”出格是他明确提出教育在增强综合国力中具有根本性职位,这是对小平同志的实现“四化”,新课程学习,科技是要害,教育是根本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出产力的思想的新成长,也是党和国度按照世纪之交国际花样变革和现代化建设两个转变面临的新课题,形成的迎接21世纪挑战的根基战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密切结合上学习和掌握根基精神,才气自觉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成长的战略职位。
1.现代经济增长纪律和国际成长经验证明,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处在先于经济增长的职位。教育对经济具有积极感化,这早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论著中就已提到。但在传统的经济成长中,教育并未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196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传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到者T·W·舒尔茨的“人力成本”理论的问世,揭示了作为人力成本主要因素的教育对付经济增长所起的不行替代的感化,并且这种感化将跟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感化的增强而日趋增强。在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到来之际,一批有重教传统的东方国度和地域,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腾飞,提供了经济成长的新模式。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总结这种历史经验时指出:“几多个世纪以来,出格在动员财富革命的欧洲国度,教育的成长一般是在经济增长之后产生的。此刻,教育在全世界的成长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成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或许照旧第一次。”教育成长对付经济增长的这种感化,不只在理论上为人们所接受,并且为实践经验所证明;不只是教育界的共鸣,也是包罗经济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鸣。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成长陈诉)中指出,对1960—1985年58个国度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表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一年,可能会使GDP增长3%。这种感化要在至少接受4年教育之后才逐步明显。《1991年世界成长陈诉)又指出,1960-1985年期间,成长中国度的产出与成本的弹性指数为0.4,即成本每增加1%,产出提高0.4%;而美国这一指数为0.60-0.75,其原因在于教育程度的差距。该陈诉得出结论:“教育促进了经济成长,并使其他成长方针得以实现。”从这个成长历程可以看出,教育在经济社会成长中的感化,是同现代经济成长中常识和科学技术感化的增强密切相关的,这种纪律也预示着教育在未来经济社会成长中感化变革的趋势。
2.世界范畴正在鼓起的新科技革命和常识经济的成长,将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糊口和国际竞争花样,教育将成为国度成长程度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符号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出产方法、糊口方法、人际交往方法以及思维方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常识更新速度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出产力的周期缩短,科技和经济越发紧密地结合,泛起一体化成长的趋势,其功效是在发家国度正在迅速鼓起常识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它的成长速度凌驾制造业,将成为21世纪主导型的经济形态。这种趋势表白,跟着科学技术的成长,经济成长对付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会下降,常识和科学技术将成为未来经济成长的决定性因素。科技革命和常识经济的成长,正在改变国际竞争的花样,成长中国度在制造业时代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比力优势正在削弱,常识、科技程度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度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艾文·托夫勒所说:“常识是敲响21世纪经济霸权大门的钥匙”。世界银行在1998年颁发的陈诉(常识与成长》中指出:常识对成长的感化已经获得普遍认可,此刻国度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常识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的成长,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正活着界范畴内引起经济成长战略的重大调解。日本从70年代的“技术立国”国策改变为“科技创新立国”,正说明了常识和科技创新在当今和未来国际竞争中的突出职位。
这种成长态势已引起了我国带领层的密切存眷,而且得出了相应的结纶。江泽民同志在全教会的讲话中指出:“此刻,科学技术在经济、国防和社会成长中的感化日益重要和突出,常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出产力的速过活益加快。如果说已往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背后,主要表示为直接争夺产业化必须的资源和商品、成本输出的市场,那么,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环绕人才和常识的竞争展开。成长的优势储藏于常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产日益向拥有常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度和地域堆积,谁在常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成长上占据主导职位。这种成长花样,对付第三世界的宽大国度来说.既提供了操作高科技和先进常识逾越传统成长模式的有利机遇,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在阐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充实注意。一度被国际社会看好的一些新型国度的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严重倒退,说明成长中国度如果过度依赖西方发家国度,如果仅仅靠操作自已的廉价劳动力、耗损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物来成长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努力提高本国的常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花样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职位,就一定进一步拉大同发家国度的成长差距。”这个论断无疑是我国对国际竞争花样变革的回应,也是迎接国际竞争新挑战的战略选择。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和科技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很多比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大多是从海外引进的。据原国度科委抽样观测,在有引进项目的220个企业中,同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相助进行吸收消化的企业只占2%,大大都企业是依靠引进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加入国际竞争,在高科技和常识经济迅速成长的条件下,面临着竞争能力下降的严峻挑战。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和常识经济的挑战,党和国度把提高科技程度和创新能力提到了干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新高度,把提高民族创新能力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到了我们面前。
提高科技程度和创新能力的根本在教育。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是常识创新、流传和应用的主要基地。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照旧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常识、技术创新成就方面,教育都具有奇特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从全国范畴内现阶段实行产业化和信息化平行成长战略,主要任务照旧实现产业化,那么.教育则在完成产业化任务的同时,更要提前为迎接常识经济时代做大好人才和常识的筹备。教育在筹备常识经济成长的前提条件(完成产业化、较高的教育普及水平、较强的创新能力)方面,都将发挥要害性感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实现产业化和迎接常识经济时代的根本工程,也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3.我国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根基国情.使教育在解决社会转型中的各类矛盾,实现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再起的方针中,占有非凡的职位和感化。我国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根基任务就是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又是在一小我私家口多、经济、文化掉队这样一种根基国情的根本上推进现代化的,这就势必使我们面临很多产业化国度所不曾有过的非凡矛盾,例如经济总量大而人均程度低;人均资源短缺而单元产值的资源耗损高;科技进步的要求火急而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人才短缺;人口多、就业承担重而大量低素质劳动者又加重了布局性赋闲,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孝敬低(1998年为32%.而发家国度一般为80%以上);人口和劳动者素质低,影响科技进步和缔造就业时机 在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素质都处于低程度的条件下,两者会形成恶性循环:科技进步会裁减低素质劳动者,加重布局性赋闲;解决低素质劳动者的赋闲问题,就要成长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会阻碍科技进步。解决这个矛盾的底子出路是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法的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变极重的人口承担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在解决这个矛盾中,教育起着要害性的感化,主要是:
(1)培养专业人才和提供常识孝敬,促进科技进步;
(2)耽误教育年限,推迟就业,缓解就业矛盾;
(3)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再就业能力,适应技术进步和布局调解;
(4)着重培养受教育者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时机。
因此,改良和成长教育在解决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根基矛盾、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方针中,具有全局性、先导性、根本性的职位和感化。
4.落实教育优先成长的战略职位,发挥教育的根本性感化。经过近20多年来的学习和实践,尤其是小平同志的深刻思想,在党的12大以来各次党代会陈诉中的论断,使全党、全社会对付教育战略职位的认识有了质的奔腾,“科教兴省”、“科教兴市”已经成为大大都地域的决策。此刻的问题是,一方面恒久占支配职位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即重物质成本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开发的问题,并没有底子转变,出产性挥霍数目惊人,而教育投入严重不敷,成为制约教育成长的主要因素。我国教育经费近20多年来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仅以1991-1998年为例,教育总经费从731.50亿元增加到2949.06亿元,增长4倍,个中财务性教育支出从617。83亿元增加到2032.45亿元,增加3.2倍。但是,教育经费的增长仍然滞舌于百姓经济的增长速度,国际上作为权衡当局对教育投人程度的指标,即大众教育经费(在我国为财务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从1991-1995年连年下降,从1990年的3.04%,到1991年的2.85%,1992年的2.73%,1993和1994年的2.52%,1995年的2.46%,直到1996年才开始回升,1998年为2.55%,1999年的比例有明显提高,但还没有到达1990年的程度,远低于1995年世界平均大众教育经费占GNP4.9%的比例:也低于欠发家国度平均4.1%的程度。因此,实现《中国教育成长和改良纲领》划定的财务性教育经费占GNP的4%的方针,只是到达欠发家国度1995年的平均程度。此刻看来20世纪末是达不到这个方针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实现这个方针,教育不只不能发挥先导感化,相反很可能会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全教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当局,都要将教育纳入战略成长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机关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常识财富和要害的根本设施,放到优先成长的战略重点职位。各级党政带领干部,都要抓好教育事情,对峙在制定经济与社会成长计划时担保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成长,对峙在布置各级财务预算时实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宁可将其他方面的工作放慢一点,也要提高教育支出在财务支出中的比例,为教育优先成长提供物质担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98年开始,持续五年中央财务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各地也仿效中央每年提高一至两个百分点。我们相信只要切实转变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调解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机关,教育经费增长滞后于百姓经济增长的状况就会改变,教育对经济社会成长的促进感化将会充实发挥,也才气为实现经济增长方法的转变缔造条件。
教育战略职位和感化发挥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教育成长程度、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教育看法和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满足现阶段经济社会改良和成长的要求,更不能适应21世纪科技革命和常识经济成长提出的挑战。教育投入不敷当然制约着教育的改良和成长,而教育自身如果不通过改良和创新加快成长,教育投入就不能充实发挥感化,同样有可能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因此,“有远见的、成熟的、及格的带领,一定是重视教育的带领。”这里讲的重视教育的带领,既要确保教育投入的优先职位,担保教育适度超前成长,还要亲自带领教育的改良和成长,真正做一个“教育省长”、“教育市长”,使教育的成长纳入经济社会成长的全局,使教育的范围、布局、体制和运行机制、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现区域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协调成长。
二、教育成长的现实依据和战略选择
建国以来,出格是改良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成长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环球公认的。仅举几例:我国1998年年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笼罩率达73%,2000年根基实现“普九”,从义务教育法颁布的1986年算起,只用了14年时间,即使从建国以来算起也只用了50年,而德国用了128年普及8年教育,日本也用了30多年才普及6年教育。如果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因素,那么,在近13亿人口的大国普及根基教育确实是伟大的社会工程,活着界教育史上也应该是光辉的篇章。我国高档教育在校生1998年到达632万人,毛入学率为9.2%(老口径为7.1%),以老口径计算,高档教育毛入学率从2%提高到7%,我国用了10年时间,而世界成长中国度则平均用了20年时间。这些事实说明我国教育成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范围的教育,为21世纪的成长奠基了坚实的根本。但是,教育的总体成长程度还比力低(例如我国1998年的高档教育的毛入学率为9.2%,低于1995年世界平均16.2%),还不能满足社会成长和人民群众对付教育的需求,积极成长各级种种教育事业仍然是21世纪初教育事情的火急任务。
我国教育成长战略选择的根基依据是教育的供求干系,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教育成长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相对不敷的教育供应能力之间的矛盾。我国现阶段的根基国情存在着拉动教育扩展范围的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基数大,年轻型人口布局存在超大范围的教育需求;
(2)经济社会因素:产业化、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人民物质文化糊口程度的提高会使教育需求向高质量、高条理教育上移;
(3)体制因素:恒久沿袭的“准干部教育”制度和包就业的人事制度,助长追求高学历的社会意理;
(4)文化因素:独生后世比重大和重学历的东方文化传统,增加了学历教育的社会压力,等等。
教育供应能力受到经济成长程度、财务支撑能力和居民蒙受能力的制约。这种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示是:
1998年我国人均大众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大众教育经费945元(折合114.4美元);1995年世界人均大众教育经费为241美元,生均大众教育经费为1273美元,在以如此低程度的投入支撑现有教育范围的条件下,如何回应社会连续增长的教育需求?这是我国教育成长战略选择的根基问题。底子出路是通过改良,扩大教育资源,同时要公道地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各类资源充实发挥感化,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有效教育需求;也就是世界银行在其(中国21世纪教育成长战略方针)政策纪要陈诉中提到的,要实现“公正、效率、质量”三个根基方针。这就需要处理惩罚好几个干系全局的干系:
1.普及与提高的干系。 主要是指义务教育与高档教育的干系。从担保教育公正和提高民族素质的角度,普及义务教育无疑是根本工程,国度也明确把“普九”作为教育事情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迎接常识经济挑战,创建国度创新体系的角度.高档教育在提高民族创新程度和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居于非凡的职位,尤其是在“普九”方针逐
[1] [2] [3] 下一页